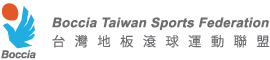
Boccia五四三
2013.10.15
我是殘障運動分級師(上)
文 / 謝正宜 (轉載自臺大醫學院【楓城新聞與評論】230期電子報醫學專題版)
我是誰
我是個復健科醫師,我在醫院裡的門診和病房照顧病人,這樣的臨床工作主要的信念是提升功能。例如,中風的病人半身癱瘓,病情穩定卻無法行走或自理生活,我和我的團隊一起來幫他增加行動及生活自理功能;如果病人要回歸社會,我和我的團隊一起來幫他找到適當的行動輔具,建議相關的環境改造。有些兒童自幼即有疾病,影響各項功能的發展,我們一起來幫他學得個案年齡該有的功能,或找到代償的方法,全面提升個案的能力。以腦性麻痺這個疾病而言,動作的發展是最大的困難,幼兒早期,團隊主要在訓練坐站走路功能、家長照顧的技巧;近學齡的時期,無法行走的兒童需要開始學習行動輔具,寫字困難的兒童需要電腦輔助;隨著生長,有些個案需要藥物來增加或維持功能,有些需要骨科手術。無論是哪一種疾病,儘可能增加或維持病人最佳的功能就是我們的工作。
地板滾球(Boccia)讓我大開眼界
2006年之前,我的生活都是繞著病人打轉,看病、教學、自我學習。病人和運動競技在我的腦海裡不曾有交集,殘障運動也只是書上看過的名詞。2006年有一天,我應朋友之邀去看腦性麻痺的地板滾球(Boccia)。那是在宜蘭一個身心障礙全國運動會會場,我第一次看到重度腦性麻痺以輪椅代步的孩子比賽地板滾球。想像這樣的場景,重度動作障礙的個案,控制肌肉協調、舉手、握球是何等的困難,再加上要精準的將球投擲出去贏得比賽,那種認真、執著的態度,和我們熟悉的任何運動比賽選手一樣,且更令人驚歎他們的表現。
地板滾球原是古代的宮廷遊戲,經過修正後,地板滾球成為一種使用極少的肢體動作,卻需要運用策略和技巧的活動,是特別針對重度動作控制困難者所設計的競賽活動,亦於1984年列入殘障奧運 (帕奧Paralympics) 的比賽項目中。比賽所使用的場地大小為 12.5公尺長、 6公尺寬的平坦地面 (和羽球場一樣大),一般國際賽事的場地多租用體育館。地板滾球需要的器材包含6個紅球、6個藍球和1個白色目標球,每個球的重量是275 +/- 12公克,圓周長是270 +/- 8 毫米 (大約橘子大小)。選手乘坐輪椅進行比賽。地板滾球計分是依據比對方更接近白色目標球的總球數,勝利則是取決於每一局得分的加總。
我看到腦性麻痺選手緩慢地移動輪椅,努力的將球握好,將身體穩住,一次次的瞄準,然後將球投擲出去,來來回回一球又一球,直到比賽結束。這些我們想來輕而易舉的事,在動作障礙的個案身上是何等的不容易。我感動到回程開車的路上都在流淚,我從未想過,除了給診斷給治療給建議,還能做什麼?原來,除了界定障礙,我還能鼓勵參與,任何人都需要娛樂及運動,可以玩滾球有樂趣更重要。但我能做什麼來幫忙推廣殘障運動?就這樣一個疑惑,在兩位復健科學弟鄭舜平醫師及林傳朝醫師 (他們是殘障桌球國際分級師 )協助指引鼓勵下,我單槍匹馬自掏腰包在 2008、 2009年三度出國,完成了地板滾球國際分級師 ( international classifier) 的訓練認證,更在 2010、 2011 年受邀到葡萄牙、廣州和北愛爾蘭擔任地板滾球比賽國際分級師;而在國內我積極協助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推廣這個運動,讓病人早些接觸。
什麼是分級 / 什麼是分級師
大家都能了解運動對健康很重要,人人都可以從事運動,但要談比賽或運動競技,想到觀眾的目光、掌聲、勝利者發亮的獎牌、瞬間的喜悅表情,公平公正公開是比賽順利的前提。一般運動競技以運動員的表現為競爭重點,殘障運動先一步規範參賽者的資格。殘障運動的運動員,因有疾病在身,不利其與一般運動員競技,故另定一套參賽辦法,先確認該運動員符合該項目規定的最低參賽標準,再依比賽規則將運動員分成不同組別,同一組別運動員因病造成的能力限制相類似,所以最後勝出的關鍵是勤練耕耘的結果。這一套為比賽公平性而形成的制度,就是殘障運動的分級 (classification) 制度。
舉個簡單的例子,同樣有截肢,A是膝下截肢穿戴義肢可以站立打桌球的選手,B是膝上截肢穿戴義肢可以站立打桌球的選手,而C是兩腿缺失乘輪椅打桌球的選手,若ABC放在一起比賽勢必不公平,因為個別喪失的能力不同,而這些能力恰好影響打桌球需要的快速左右移動及平衡等能力,所以要放在不同級別或組別來比賽才公平。
各種殘障運動項目有獨立規範的分級細則,原則上,殘障運動是依照功能損傷 (activity limitation) 之不同來分級。功能損傷比較重的放在一級,功能損傷比較輕的放在一級,理論上功能損傷比較重者,其運動表現會比功能損傷比較輕者來的差。執行分級相關事務的大會技術官員 (technical official) 稱為分級師 (classifier)。分級事務在比賽前就開始,一直延伸到比賽中。分級師組成分級團隊(classification panel),成員通常為一名醫師、一名物理或職能治療師及一名運動技術專家,在賽前共同針對運動員的醫學診斷、診斷帶來的功能損傷、及功能損傷造成運動表現的影響(impacts on sports performance)進行評估,經討論後決定該運動員的參賽級別 (sport class)。比賽開始後,分級團隊要進行賽中觀察(observation in the field of play),逐一確定運動員在賽中表現符合賽前評估的實況,沒有欺瞞希望降級獲益的狀況。
國際殘障運動比賽分級如何進行
國際上有許多的殘障運動組織,各有專門規範的運動項目。以腦性麻痺國際運動娛樂協會 CPISRA (Cerebral Palsy International Sports & Recreation Association) 規範的地板滾球和七人制足球 (Football 7- a-side)為例,這兩類運動的運動員必須是腦傷的醫學診斷,如腦性麻痺或頭部外傷,造成肌肉控制不足(impaired motor control)、痙攣張力 (spasticity)、不自主動作 (involuntary movement)、協調不佳(impaired coordination)的功能損傷,且這些功能損傷明顯造成運動表現的影響,始得參賽。符合參賽標準再依各項目規定給予比賽時的參賽級別。CPISRA分級師最重要的工作是確定運動員已達最低參賽資格,再依比賽規則,考量運動潛能,將運動員分成不同級別來進行公平的比賽。
國際殘障運動比賽實際上是如何進行分級呢﹖以地板滾球為例,地板滾球有四種參賽級別 (BC 1 2 3 4) 。選手報名時就要交出有效的分級卡,若不曾被國際分級團隊分級過,或所持卡片為暫時卡,都要在賽前接受分級。單項目較大型的比賽,牽涉新選手人數較多,會設有兩個分級團隊,加上總管分級事務的主分級師(chief classifier),總共會有 7人一起工作。通常在比賽前 2到 3天,選手要依約定時間來接受分級。選手由領隊或教練陪同到分級區,分級團隊經過問診、理學檢查和神經檢查,同時實際進行數次地板滾球投擲,分級團隊依醫學診斷、功能損傷及運動表現的影響綜合討論,決定該運動員是否符合參賽標準及其參賽級別。由於分級過程必須詳實記錄以免未來爭議,分級團隊相互支援彼此了解的默契非常重要。在不到30分鐘的評估中,我(醫師)提問的時候,務必確定選手可以懂,而我的伙伴幫我記載清楚問診重點;我做肌腱反射檢查,得到兩個加號或4個加號、痙攣張力指數多少,我要清楚做出來或說出來,讓別人看得懂聽得懂;而當治療師伙伴測肌力或關節範圍時,我要覆誦且記錄正確;當技術專家伙伴測抓握控球能力及投擲表現時,我也要幫忙寫下來。有時真覺得,遇到投緣的伙伴,一個動作帶到一個數字,清清楚楚,一切盡在不言中呢。分級進行中,絕大多數選手非常緊張,如何讓選手儘可能放輕鬆且全力配合檢查,常就是資深分級師的功力,也是我不斷在學習的重點。最後,依照我們看到的病況對該運動的影響,給選手一個級別來排賽程。比賽正式開始前,所有選手參賽級別要公告以求公正公開。
比賽正式開始後,分級團隊要進行賽中觀察,配合先前的分級紀錄,逐一觀察選手,仔細比對來確定選手賽中表現符合賽前評估的實況。有些選手在賽前會因過度緊張或故意隱瞞,在分級時被判定有較多的功能損傷,一旦上場爭決賽資格,選手的真本事在場外一覽無遺,經錄影存證並向選手及教練說明清楚後,會從下一場比賽開始更改級別,有蓄意欺騙事實的選手會有禁賽的可能。分級師若觀察到任何疑慮,要請主分級師複核或必須找時間再次請選手到分級室複查。整體比賽結束時,運動員會拿到分級卡供下次報名參考。如果選手已多次參賽,經多次分級團隊評估,認定分級不會再變,可以拿到永久卡(confirmed status)。
如果是腦性麻痺七人制足球,選手是腦傷但能進行跑跳運球者,有四種參賽級別 (FT 5 6 7 8) 。分級團隊同樣在室內看選手的醫學診斷、功能損傷,再來我們一起到戶外經過設計的模擬小場地,由技術專家測試足球相關的跑、跳、踢球、運球能力,同樣的經過討論,共同決定是否符合參賽標準及其參賽級別。真正比賽開始,分級團隊要坐在高高的看台上,用望遠境仔細確認分級正確。用望遠鏡追著某一位選手,還要看到運動時疾病診斷對動作的影響,我是需要再加強訓練的。對眼睛不太好的我這是一種挑戰,我常是好不容易找到選手,低頭看一下分級紀錄,一抬頭又不見人影,整場下來眼睛好累手好痠,還曾發生不知道球已經朝我飛來,硬是被球打到。
抗議 Protest和抗告Appeal
抗議 (Protest)和抗告(Appeal)是分級師最不喜歡聽到的字,但這也是很重要的監督機制。「抗議」是指對「分級結果」不認可,可以正式提出表態並期待說明。抗議可以是選手自己不同意分級結果 (通常是覺得自己比較嚴重,要分在嚴重一點的級別),可以是某國對他國選手分級結果不認可 (通常是覺得這位選手比較輕,要分在輕一點的級別)。抗議有一定的時間點和流程,一旦提出抗議且經大會窗口受理,這位選手會在最短時間內由第二組分級團隊再覆核一次,這次的覆核即為最後結果。大家可以想像,國際級的賽事茲事體大,不論覆核結果如何總有不滿聲音,無形中更增加分級師必須審慎行事的自我要求。主分級師每每在行前會議都會耳提面命“try very hard to do it right, and better right at the beginning“。
「抗告」更累了,這叫分級師的夢靨,這是選手對「分級過程或程序」任何不滿,正式提出表態並期待說明。例如選手覺得分級中不受到尊敬,或覺得抗議處理流程有缺失等等。抗告也有一定的時間點和流程,一旦提出且經受理,賽後直接由荷蘭海牙法庭仲裁。從受訓到上任,主分級師總是提到抗告的煩擾,要分級師們嚴守行為守則(code of conduct),遵守分級標準作業,言行舉止小心謹慎,避免惹禍上身。
繼續閱讀:
我是殘障運動分級師(下)
